“為了投低空,老板讓我去學飛機駕照”
今年,低空經濟的熱度正在加速一些戲劇化的事件發生,雖然這個世界并不缺少匪夷所思的故事,但最近聽到的幾個信息還是讓我受到了一些沖擊。
首先,某國資PE在內部高調宣布低空經濟為今年下半年唯一確定性的投資主題,為了更好的了解低空經濟的相關知識,竟然要求員工去考飛機駕照,而且是自費的。當然,這個無理要求并沒有得到大家的響應,可這確實也說明低空經濟讓一些常規動作變形了。
其次,據報道,西部一個剛剛摘去貧困縣“帽子”的地方政府,希望當地的一家運營商力,支持當地發展低空經濟。其實,當地除了地廣人稀,發展低空經濟真沒有什么前途。
第三,我們前兩年寫熱門賽道時,總會用這樣一種說法,就是幾十家機構爭搶一個項目,半導體如此,新能源、新材料亦是如此。雖然在如今資金有限,風險放大的現在,這一幕很少出現了。
但在低空領域最火的eVTOL賽道,這種故事還是重演。
以今年融資動作最頻繁的沃蘭特為例,為了更高效率的見投資人,他們每周都會有一個專門的下午來做路演性質的宣講,而參與的投資人人數從最初的十幾個人慢慢變成了上百人。
用沃蘭特CFO黃小飛的話說:“今年3、4月份,我基本上每個月要咳好幾場,辦公室永遠都備著枇杷膏和各種各種噴嗓子的藥。”正是在這種強度和頻率下,市面上幾乎所有的機構、二百家地方政府、券商都對沃蘭特盡調/調研了一遍。
低空經濟,新瓶裝舊酒
低空空域,通常指距正下方地平面垂直距離1000米以內,根據不同地區特點和實際需要可延伸到3000米以內的空域。
“低空經濟”則是以低空空域為依托,以通用航空產業為主導,涉及低空飛行、航空旅游、支線客運、通航服務、科研教育等眾多行業的經濟概念,是輻射帶動效應強、產業鏈較長的綜合經濟形態。
其中低空經濟產業的核心部分為主機廠,即低空飛行器制造企業。目前主機廠對應的飛行器包括以下四類:消費級無人機、工業級無人機、傳統通航飛機 (傳統固定翼飛 機、直升機等)、eVTOL。
其實,中國的低空經濟早已初現雛形。中國造的無人機不僅是世界第一,而且在生產能力和成本上均遠超世界第二。據不完全統計,到2023年底,我國民用無人機研制企業超過2300家,量產的無人機產品超過1000款。2023年,我國交付民用無人機超過317萬架。
所以,低空經濟嚴格來說是一個新的提法。但實際上不管是通航行業還是無人機行業,它一直都是存在的,行業發展也經歷了高峰和低谷。
2021年2月,“低空經濟”這一概念首次被寫入《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
今年,“低空經濟”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明確積極打造這一“新增長引擎”,也讓低空領域迎來了空前的熱度。除了政府報告和多部委的相關規劃外,北京、廣東、安徽、山西、四川等多地都制定了政策細則以推動低空經濟發展。
緊接著二級市場先炒為敬,最夸張的時候都炒到了座椅的這種供應商,就連平時在A股長期虧損的朋友也開始得意地說,靠著低空經濟的熱度回了一波血,賺了錢。
一級市場雖然比二級市場理性很多,但也絲毫不影響低空領域項目的熱度。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6月底,該領域已經完成了9筆融資,比去年一年數量還多。與此同時,賽道明星企業沃蘭特從今年3月到6月,接連官宣了三筆融資,每筆規模都達到億級,更是把整個賽道的火熱拉到了一個新高度。
另外,在本次與項目方的交流來看,越來越多的投資人開始主動來找低空賽道的項目,有些企業甚至被動開啟了新一輪融資,而接觸的項目方也都是大幾十家的數量。
從投資出手數據來看,目前大部分投資都集中在主機,個中邏輯也不難理解,可以參考蘋果公司一家就占了蘋果生態鏈市值的90%;特斯拉占特斯拉生態鏈市值的60%。但至于大家投的作業無人機、物流無人機、載人eVTOL等具體標的,對應汽車領域的是乘用車、輕型商用車、大巴車、卡車還是軍車,則見仁見智了。
在庚辛資本合伙人張家康看來,在低空經濟領域,宏觀層面大家已經沒有分歧了,分歧主要體現在微觀層面。體現為投資人掃完賽道后可能會走向兩個極端:過度樂觀,或者過度悲觀。我們認為兩者都是因為忽略了一些事實導致的。
一種是過度樂觀。以為低空經濟就是在現有的無人機基礎上簡單升級,對飛行活動的嚴肅性、研發門檻和監管要求的理解比較簡單,對產品的經濟性、安全性、效率要求想當然。
這類投資人的風格和許家印造車很類似,恒大做地產一度是中國最成功的,就以為全國這么多銷售,就可以保證年銷500萬臺車了。類似這樣,拿其他行業的內在邏輯硬套航空業是容易誤判的,航空業對安全、經濟和效率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另一種是過度悲觀則認為低空很難有什么新應用,目前都是政策揠苗助長的虛火。
虛火還是真熱,數據最能給出答案。
根據中國民用航空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到2025年,中國低空經濟的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1.5萬億元,到2035年更是有望達到3.5萬億元,10年復合增長率達8.8%,這是一個能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的龐大市場。
但說到底,低空領域的很多項目還處在早期,從融資階段來看,大部分項目還停留在B輪前,只有極少數項目融到了C輪甚至D輪。從估值來看,行業平均水平還在小幾個億的級別,十億以上的項目少之又少。
而與早期項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市場上對整個賽道和項目的關注度早已超過了行業本身的發展階段。這種對比反映在融資動作上則是超額認購,一般為三到六倍不等。
談低空經濟,人們首要關注的就是場景。
卓翼智能董事長任雪峰分享稱,在實際應用場景上,低空領域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無人機的行業應用,包括應急消防、測繪,工業巡檢,農業,目前來講技術相對成熟,場景落地較好,各個廠家都在提供更優更廉價的解決方案,更有性價比的解決方案,這個場景也是卓翼目前發力的主要方面。
第二是物流領域,這個場景的市場潛力是巨大的,技術也相對成熟,但是礙于空域沒有開放,不能形成端到端物流的空域管理,同時成本較高,目前政府采用大量補貼的方式來促進行業發展,但補貼能堅持多長時間是未知的。第三則是現在最火的eVTOL載人,這個體量是最大的,也是難度最大,耗時最長的。
在這之中,最熱最具商業化的細分賽道就是eVTOL了,這個摩根士丹利發布預測,到2050年全球飛行汽車市場規模將達到9萬億美元,其中中國潛在市場規模將達到2.1萬億美元。
在發展路徑選擇上,eVTOL廠商一般可以分為兩類:先貨后人和只做載人的。相對來說,前者可以較早的看到營收,后者則更需要依靠融資能力。在交流過程中,不止一家公司跟我提到持續融資是公司的頭等大事,甚至說是唯一正經事也不為過, 畢竟拿不到錢就意味著率先出局。
這里需要科普一個知識是,在飛行器在商業化前,必須要拿到三個證,分別是:
1. 型號合格證(Type Certificate,簡稱TC):這是證明產品設計安全可靠的證書,是適航認證中最早開始且難度較大的一環。
2. 適航證(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簡稱AC):也稱為單機適航證,意味著航空器合格證,可以交付使用。
3. 生產許可證(Production Certificate,簡稱PC):工廠生產的質量體系完善,生產出來的都能滿足要求。
經常描述的“適航取證” ,實際上就是TC取證,TC是獲取難度最高的證會占到三個證里80%的資源和精力。但載貨和載人的適航證的取證難度也不一樣,不過從資金投入、時間成本還是安全等級上,很顯然載貨的會更加容易。
時的科技創始合伙人蔣俊提到,eVTOL研發成本其實并不高,在5到10億人民幣,但eVTOL飛機不會像新能源發展那么快,迭代速度也相對較慢,這是因為飛行器的研發過程中需要民航局深入的參與和介入,要做的安全相關驗證工作也比汽車要多得多。
此外,時的科技就是只做載人eVTOL的主機廠,在應用場景上也非常明確:旅游觀光和空中的士。按照時間表來看,時的科技最早在2026年完成取證,2027年開始商業化。
也有從業者指出這個時間表有點激進了,畢竟現在eVTOL場景中的基礎設施、法律法規還不完善,他甚至直言身邊所有傳統航空圈的都不看好eVTOL。
的確,在適航取證之前,這類廠商是幾乎沒有收入的,所以他們會尋找所謂的耐心資本,支持他們走到取證,走到產業化階段。eVTOL作為新型的高端飛行器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并不代表說低空經濟有很長的路要走。
1%的出手率
即便熱度高漲,但受一級市場大環境的影響,投資人依舊比較務實,關注點聚焦在營收、利潤、落地和基金收益上。
其實,低空區域中的很多細分賽道還是比較偏美元邏輯的,風險相對較高,投資回報周期長,更適合早期的VC,這樣一來,對于抗風險性差,更重短期投資回報的機構來講,低空賽道并不是首選。
除此之外,由于當下退出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在低空投資領域,以退定投還是比較典型的一個策略,反映到投資動作上,就是偏好營收和凈利好的項目,而這樣的項目其實是少之又少的。
在團隊背景側,從去年開始,航空業背景的團隊明顯更受投資機構青睞,原因在于當前各界在低空經濟發展的看法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也是我國在航空領域彎道超車的機會,而彎道出現的時候,往往是由專業選手下場收割果實,從安擎科技創始人劉瑩的反饋來看也印證了這一情況。
但不管是營收凈利好還是航空背景的項目,在當前的項目池子中都是少之又少的存在。
基于以上兩點,也就有了看的機構多,出手機構少的現狀。一種比較直觀的對比是,可能有一百家機構在看機會,但實際出手的只有一家。
在融資側,今年還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就是產業投資人、各地產投基金就一窩蜂的涌了進來,這也讓賽道中的企業有點措手不及,而且并不是只有經濟發達的地方率先發力,而是全國各地都有,甚至每天都接待不停。
正是如此,今年官宣融資的eVTOL廠商基本都拿的是政府的錢,比如沃蘭特最新一輪拿的是自貢區的,覽翌航空拿的是合肥的錢。
另外,由于主機廠在生態中的核心地位,長三角或珠三角很多地方都會對企業提出更苛刻的要求,比如只能選擇拿一個地方的錢。
當然,除了吸引了大部分關注度和資金的主機廠外,現在很多機構選擇去產業鏈的上游去找投資機會,包括材料、電池和零部件等。
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或者國資平臺都堅定的看好投入和風險雙高的主機廠,在交流過程中,也有投資人表示他們只看上游,因為他們返投任務不重,更多的是想博回報,上游的項目至少能夠在這個大背景下做到旱澇保守。
中科創星創始合伙人米磊也提到,由于已經在eVTOL和無人機領域完成了率先布局。
中科創星就把精力放在關注新涌現的整機廠及產業鏈上游供應商。
各地政府,機會平等?
一位投資人告訴我“做載人的都在上海,做無人的都在深圳,軍工在成都和南京,高精尖的技術和空域服務在北京”,似乎在中國這么大而不平均的條件下,低空經濟在各地的發展是割裂的,也有各自的偏好。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長三角,珠三角還有其他一些低空經濟的試點地區外,云南、貴州那邊的很多地方對低空經濟也很積極,給出的政策也比較誘人,但其實他們的資源稟賦可能并不算好。這就有了開頭,西部貧困縣也想搶占低空經濟先機的案例。
而出現這兩種現象的原因則在于,各地政府在發展低空經濟上的優勢和切入點不同,但面對的機會是相同的,大家都想當低空經濟里的下一個“合肥”。
不止一位從業者表示,現在沒有哪個地方呈現出了絕對的在低空領域的集群效應。
張家康認為,各地低空整體的底子都很薄弱,能夠形成集群效應的前提,是有強大的鏈主和產業鏈。目前還太早,能看到各地都在培養自己的鏈主和產業鏈核心骨干成員,但大家的邏輯都不同,側重點不同,甚至有些分道揚鑣,都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但過幾年差距會越來清晰。
任雪峰也提到,對于政府來講,有些能力是必須發展的,比如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是不分區域的。但在具體場景上需要因地制宜,舉例來講,新疆專業人才不多,也沒有較強的供應鏈優勢,但它仍有差異化的機會,就是它能提供豐富的場景,因此也有很多企業愿意到新疆去設廠,這就是典型的靠場景吸引企業的方式。
劉瑩認為,評價一個地區的低空經濟至少要分兩個角度,第一是有沒有一些頭部的廠商,第二是區域自身有沒有飛起來,有沒有用起來,也就是說所以發展低空經濟,運營是關鍵。她還提到,因為大家面對的都是1000米以下的低空區域,是同樣的生產資料,所以每個地區的機會是平等的,不過不同的要素會造就不同的產業形態。



 獵云網
獵云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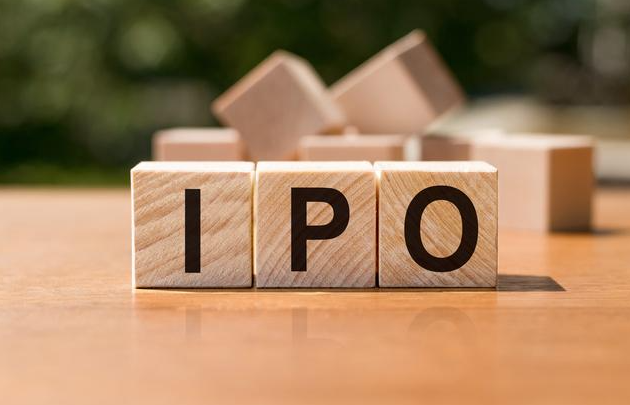
 東四十條資本
東四十條資本
 融中財經
融中財經

 博望財經
博望財經



